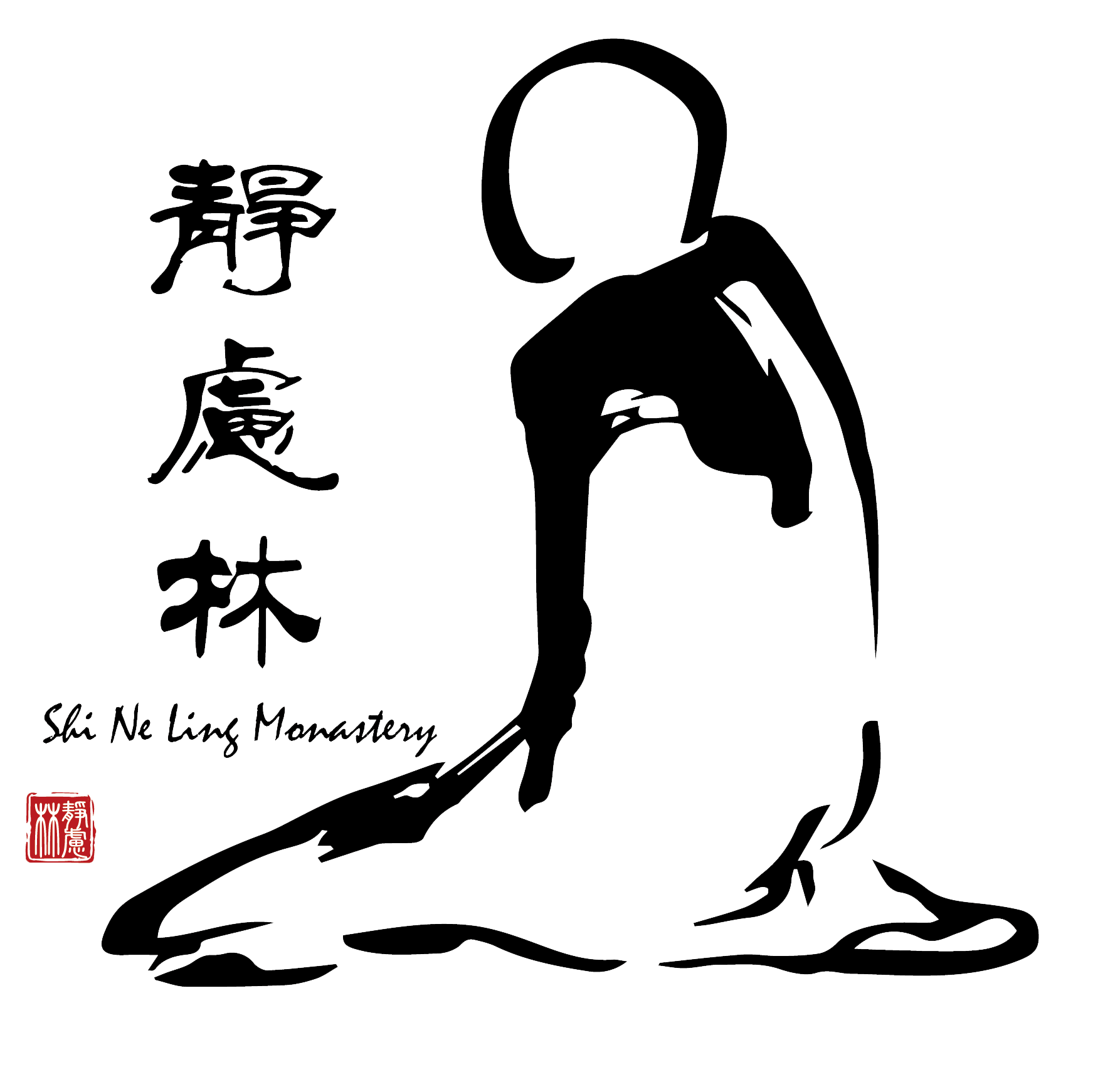隆波帕默尊者
Luangpu Pramote Pamojjo
2024年9月21日|泰國解脫園寺

我們學法已經很久了,有些人學了幾十年,有些人從年輕時便開始學法,直到年紀漸長。在很多寺廟,大部分見到的都是上了年紀的人,他們從年輕時就開始進寺廟,一直到老。很多去寺廟的人,有些人獲得利益,有些人沒有獲得利益。但能真正明白法、真正深入領悟法的人,也頗難覓得,依然還有,並非沒有,取決於我們的用心,要訓練自己到何種程度。
有些人的生命出現了問題就進來寺廟,當問題過去了,就懈怠了。有些人很用功修行,但當人生遇到問題時,就沒力氣修行下去了。
訓練自己的工作是很難的、提升自己,修行並不是其他的工作,而是「提升自己」的工作。因此,要真的很忍耐才可以做得到。當有苦,心很氣餒,無法修行下去時,一定要忍耐。有苦要修行;有快樂也要修行。
人的自然狀態就是——當有快樂時,就陶醉其中,以此為樂。因此,並非「法」不好,而是學法的人不太好,不夠堅強、不夠堅決。這是沒辦法批評的,取決於每個人累世所積累的波羅蜜不同。
有些人投生在富有的家庭,父母慣著他,想得到什麼,就會得到一切,然而他卻看到苦和過患,感覺天天快樂,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,如此之人波羅蜜極高。比如:耶舍尊者,作為富家子弟,卻覺得歌舞表演沒什麼實質的意義;優婆底沙(Upatissa)、拘律陀(Kolita),即:目犍連尊者和舍利弗尊者,也是富家子弟,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享受歌舞表演,有什麼就隨心遊玩。然而有一天,看到這樣平白浪費生命沒有實質的意義,「平白浪費」意思是: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,沒有什麼好處,有趣嘻嘻哈哈也只是一瞬間,很快又會回到原來的苦了,這是極具波羅蜜、極具功德之人的例子,他們的生命真的很舒服無憂,但是他們放下了世間的快樂來修行。
悉達多太子在世間的生活亦是過得富足舒適,但他捨棄了世間,以找尋更殊勝的東西。有些人的生命很困難,為了生計當乞丐,謀生的方式什麼都有。有人患了痲瘋病,淪落為乞丐,看到很多人來到寺廟,便也跟著進來寺廟,打算待會進寺廟了,當他們分發食物時,就會得到些食物,就只是這麼想而已,進到寺廟來找食物。但那時佛陀說法尚未結束,大家還沒有去吃飯,在坐著聽法,於是他也坐著聽法,聽了之後,他就見法了。他的生活很艱難,而進到寺廟壓根兒沒有想著要學法,然而他的福報波羅蜜足夠成熟,稍稍聽聞些許觸動心的法,便豁然明白。
這些事情難以表述,我們並不知曉自己原來的資本有多少。有些人具有智慧方面的資本,但是佈施方面不太落實,他就會是一個具有很多智慧之人,但在物資方面卻較為缺乏。有些尊者衣食豐足、資具充裕,每一位高僧大德都是不一樣的。
隆布敦長老具有無比的智慧、非常厲害。他具有很多智慧,不僅能幫助自己,還可以幫助弟子,可以教導許多弟子,甚至連隆布曼尊者都讚譽他很有智慧。隆布敦長老極具智慧,他教導弟子的能力很強,但是他比較貧窮,在飲食、資具方面比較匱乏,因為過去蘇林府的居民較為貧窮。隆波曾經常常去頂禮他,坐在他的腳邊,看到他的袈裟補了又補。
每一位尊者各不相同,有些高僧大德過得如同國王一般,他沒有要求、沒有飢餓,但護持他的人卻很多,他也沒有黏著於什麼,但他的食物、用具皆非常殊勝,這就是區別。
什麼令他們有所區別?他們同樣抵達純淨無染,但依然有所區別,「業」決定差別,「業」令眾生有差別。有些尊者強調智慧,不關注佈施;有些尊者著重於佈施,不願意開發智慧;有些尊者既佈施又開發智慧,每一位不儘相同。
因此,高僧大德教導:「所有的善法,如果有機會做就做,沒有什麼不好。如果有機會做,那就去做。」隆布敦長老如此教導,他沒有教導我們沉迷忘我地去做、愚昧地去做或飢渴地去做,那樣僅得到些許功德而已,沒有帶著覺性、沒有帶著智慧,不知道什麼應該、什麼不應該、做至何種程度……因此,這些善事有機會做就去做,如果機會錯過,尊者說不做也可以,不做更好,好過於掙扎。
比如:現在水災,很多人伸出援手幫忙,如果我們沒有金錢、沒有物資可以捐助,但看到他人救濟幫忙,我們的心歡喜、滿意於他人行善,我們也可以得到功德,稱之為「隨喜而獲得的功德」。
因此,不用花錢而得到的功德也有,比如水災,這裡也有幫忙運送物資、捐錢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,能幫多少就幫多少,有機會就做。如果沒有機會就不用做,可以做其它的。
善法是重要的,做功德也是好的,把它當做依靠。善法是沖洗我們內心的工具,可以跨越生死輪迴,有機會做功德就去做,沒有機會做功德的話,就做善法。
如何才生起善法?要有覺性。何時有覺性,何時心就已經是善法了;何時缺乏覺性,心就不是善法,因此,覺性是至關重要的,我們要訓練。
覺性非常重要,佛陀甚至說:「如果還有人修習四念處,法就不會消失,就依然可以通過修行而證悟道果。」但如果僅是缺失覺性,法就會淡然無味,就會變成世間法,變成了做功德佈施、做各種好事之類的。
我們來到這裡,要訓練直至能有覺性。但在訓練覺性之前,先要用心持好戒,如果戒缺失,然後我們宣說自己有在發展覺性、開發智慧,這是盜賊的智慧——我們破了戒,然後以「法」做為藉口,假借那個原則、這個原則來欺騙世人。
因此,起先必須要持五戒,用「必須」這個詞,而不是用「應該有」這個詞。五戒必須具備,八戒應該偶爾持守。看到嗎?層次不同,但五戒必須具備。
出家人也須持守五戒,以前曾聽隆布敦長老批評有些出家人,炫耀自己有227條戒,但卻忘了五戒。因此,五戒是必要的,認真持守,刻意回避做五條不善業。「有意避免」稱之為「cetanāviratti」 這是戒的核心,要用心,然後努力發展覺性。
覺性源於心牢固地記得境界,覺性無法透過命令讓其生起。我們無法命令讓覺性生起,因為覺性是無我的,心也是無我的,命令不了,但可以在因地上播種。
讓覺性頻繁生起的因,就是「心牢固地記得境界」。這不是一般的覺性,這是四念處的覺性。一般的覺性,比如:做事不走神或忘記、走路不跌倒、開車不撞其它車子……然後宣說有覺性,這是世間的覺性。但重要的覺性是四念處的覺性,是覺知自己的覺性,知道自己身心的覺性。
身體的狀態是境界,感覺、念頭、心方面的感知也是境界,稱之為「名法」。我們有覺性憶起色法,有覺性憶起名法,這即是「修習四念處」,這就是四念處和一般覺性的區別。
四念處是努力知道自己的身心,而非知道其他的事情,並非知道外在,而是努力返回來覺知自己。但若我們嫻熟,知道外在亦能修習四念處,然後也可以看到三法印。但是它有風險、有危險。比如:我們去看美女,我們宣說以觀看選美比賽來修四念處,問說:做得到嗎?觀看選美 然後修習四念處?做得到,如果我們足夠嫻熟。
但大部分的人做不到,當看到美女,心就跑到美女那裡去了,沒有覺性。因此,向外看存在風險,
所以高僧大德才指導我們返觀自己。經典闡述:內在的法、外在的法、遠處的法、近處的法……事實上,觀內在也可以,觀外在也可以,但如果向外看,在沒有高僧大德的監督之下,出錯的概率會很高。如果我們觀自己的身心,煩惱習氣就不敢囂張。
比如:我們覺得自己是美人,我們來看自己的身體,持續地觀察下去——它真的美嗎?身體它就像一個袋子、一個皮囊,有很多孔,大的孔有九個,小的孔則遍布全身,數也數不清,每一個孔,無論是大孔還是小孔,皆有污穢物不斷地流出,我們有覺性感覺自己的身體,就看到了身體的實相——身體並非美麗、漂亮之物。有覺性不斷地感覺身體,身體是污穢不淨的,如果看到這一點,心就會獲得禪定,得以克制貪欲蓋,也就是能克制「蓋障」中的「貪欲蓋」。
然後如果我們不斷地提升,我們觀下去,我們就會看到身體充滿著無常,呼氣之後,必須換成吸氣;吸氣之後,又必須換成呼氣;行、住、坐、臥都要不斷地變換姿勢;動、停之類的,它在身體裡一直存在……我們有覺性不斷地覺知身體,它就會超越不淨的層次,進到更深一層——即看到三法印。
「不淨觀」是有好處的,它可以克制淫欲、欲貪,但如果我們能看到身體的三法印,它就會鬆脫執取,就會不再執取。
我們的身體是無常的。看嘛!它恆常嗎?哪裡恆常?呼氣了之後(要吸氣),它是無常;吸氣了之後(要呼氣),它也是無常。站了之後要走、要坐、要躺,要變換姿勢;躺了之後,還得要左翻右翻……我們持續知道身體,它有的只是無常,它為什麼無常呢?因為它一直被苦逼迫,坐久就苦,走久就苦,躺久也苦。因此,這個身體就好像一隻鹿或一隻山羌,被「苦」也就是一群獵犬整天不斷地追咬,就必須拼命奔跑、逃跑,一直逃跑,直到身受重傷,跑不動了而倒地死去。
身體也是一樣的,整日被苦啃噬折磨,我們就努力不斷地對治、努力不斷地治療:坐久了酸痛,我們就換姿勢;太熱了難受,當太熱時就去洗澡……我們努力地去對治,為了讓身體能生存下去,就像鹿拼命逃離獵犬的追捕,苦無時無刻不在追咬折磨。但是逃不掉的,最後傷會越來越重,當年紀大了,全身都是傷。我們的臉也有傷,有魚尾紋、面部鬆弛、面部皺紋,這些肌肉和皮肉都被抽乾了,直到全身都起皺,這是被時間之獵犬追咬所留下的痕跡和傷疤。
不斷地觀下去,這個身體沒有什麼實質的意義,它是無常的,它不斷被苦逼迫,有一天沒力氣跑了就會死,就像那只被獵犬追咬的鹿,在被多次追咬,最後力竭倒地,獵犬就撲過來啃食它的肉。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的,不斷被苦折磨。有覺性持續覺知,就會看到身體並非殊勝之物,身體僅是苦聚,僅是必須要照顧的負擔。
以前隆波尚未出家,隆波不太擅長觀身,因為擅長觀心,但心自行省思身體,省思下去,它就會自己感覺到——從頭到腳皆是負擔。
頭上的負擔有哪些呢?要洗頭,有些人還染髮,必須打理頭髮,整那樣的髮型、這樣的髮型。頭髮白了怎麼辦?有必須照顧的負擔。頭髮掉了怎麼辦?有些人年紀輕輕,就已經有一撮撮的頭髮掉了,苦嗎?苦!這是身方面的苦?還是心方面的苦?心方面的苦。頭還沒苦,但心已經苦了。
隆波覺知身體,然後覺得這個身體有很多負擔。早上醒來之後,必須做些什麼?必須洗臉、洗澡、排便,做完還必須準備穿衣打扮,穿戴整齊後就出門。為何需要坐車?帶什麼去坐車?就是帶身體去坐車,心不用坐車的,心想到美國,它立即就到了,但是這個身體,它必須得背著走,它是個負擔。
然後逐一看,從頭到腳都是負擔——腳指甲長了要剪,灰塵、髒東西進到指甲縫就要摳、要洗、要清理……這些都是身體上各種各樣的負擔,「bhārā have pañcakkhandhā」五蘊皆苦,這還只是一個蘊,僅是色蘊,只是這一個身體而已,苦已經數不清了。
有時候醒來,唉!眼睛乾澀,今天眼睛乾澀,眼晴又不舒服了……今天醒來耳鳴,耳朵又不舒服了……今天醒來呼吸不太通暢,身體阻塞,呼吸不通……充滿了負擔,要不斷地伺候這個身體,找飯給它吃,吃完飯了,還要帶它去排泄,一味地吃也不行。哎!那時心回來觀身體,它感到噁心、厭倦——這個身體真令人討厭!心感到厭惡。
結束後心進入另一個階段,心具有更多的智慧。身體必須去謀生,而心卻沒有去謀生,反而替身體煩惱。身體需要吃飯,身體自己會去賺錢買飯,身體自己把食物放進嘴裡,並自己咀嚼,然而心卻替身體感到厭倦。身與心是不同的部分,身體苦,身體有負擔,心僅僅只是觀者,為何要去干預身體呢?
隨著修行越來越深入,一開始看到身體是不美、不漂亮之物,接著我們就看到它僅有負擔而已,心便厭倦。當心對此厭倦了,心就會想:如何才能擺脫這個身體?擺脫不了呀!身體還存在,它還沒有死,還不能擺脫,那就必須要跟它在一起。就像我們與某些有毒的東西共存,但卻無法逃離,就像有些人的家靠近垃圾堆,像山一樣高的垃圾堆,想搬到其它地方,但還沒有能力搬遷,就必須和它共處。跟它在一起了就看到苦,看到很多過患。
身體充滿著垃圾,丟進去的垃圾很多,我們往裡面丟,直到它滿溢,它就必須排出來,看著看著……唉!這個身體苦啊!
身體苦,它有抱怨過嗎?身體從未抱怨過,但是身體向我們展現損壞和衰老,但是不抱怨,它老給我們看、它病給我們看、它死給我們看,但它不抱怨。心沒有隨著身體一起老,沒有與身體一同病,也沒有隨身體一起死。但心卻喜歡抱怨,身體稍微有些不適,心就會抱怨、散亂、不安,心是個麻煩的傢伙。
我們覺得身體有負擔,比如:我們的頭,我們必須梳理頭髮,但心會幫我們梳頭嗎?心並沒有幫我們梳頭,是身體自己在梳理。當我們梳頭時……哎呦!好無聊!心替身體感到無聊。身體沒有抱怨,而心卻抱怨。
慢慢看,然後將它分離。隆波修習了,它就分離——嘿!這個身體苦,但是心苦不苦,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如果我們訓練好了,心就會從身體中解脫出來。身體隨著自然法則而苦,它老、病、死、飢餓、冷熱、飢渴、大便、小便、酸痛……身體裡面蘊含無數的苦,心就只是知者、觀者,並沒有迷失於喜歡或不喜歡它。
因此,當佛陀教導時,祂說:對他的弟子們而言,苦可以觸碰到他們的身體,但無法觸碰抵達到心。但一般的凡夫或沒有學過法的人,當身體苦時,心也會跟著苦。
因此,我們來發展覺性,不斷覺知身體,看到身體是苦和過患,接下來我們的覺性更強大了,我們就會看到——心是分離開的。覺性及時地知道——心是分離開的,它不斷地在造作,一會兒替身體抱怨、一會兒迷戀身體、一會兒抱怨其他的事情、一會兒去愛其他事情、去恨其他事情,混亂不已。
因此,這些造作、掙扎、混亂都源於心,身體就只是物質,不是人、不是眾生、不是我、不是他。因此,問題已不在於身體了,真正的問題在於心。隆波在遇到隆布敦長老之前,就看到這一點了,看到真正的問題在於心,身體僅僅只是物質而已,它並沒有因誰而苦。
我們如何才可以學習更高層次的業處?觀身體,然後僅看到苦,有一天……
講一個故事,讓大家早上提提神。
有一天在打坐時,然後出現禪相,看到一位年邁的長老,瘦瘦的,很老,他拿著一個不知名、圓圓的水果,像這麼大,遞了過來。他給,隆波就伸手去接,但長老並沒有(馬上)給,長老先說道:「這個水果是甜還是酸,取決於裡面的果肉;心是好還是壞,取決於心本身,取決於它的內在。如果裡面仍藏著煩惱習氣,它就是壞的。」然後長老就遞水果給隆波。
然後當時隆波並不知道這位長老是誰,大概過了一年,去頂禮隆布敦長老,(才發現):哦!原來是這位長老,他曾經教導隆波關於心的事情:人是好是壞,取決於自己的心,他教導這點。
在謁見隆布敦長老本人之前,曾經讀過三攀他旺寺廟的一本書,是關於隆布萬尊者的佛牌圖鑒,由三攀他旺寺廟印刷出版。最後一頁有一處空的地方,內容與這本書無關,不知道印製的人為何把它放上去,有人讀了這一段內容而從中受益,然後跟隨隆布敦長老學習。
隆布蘇金長老,認識嗎?隆布蘇金·素錦歐長老,下個月尊者也會來這裡,一年一度在生日時,邀請他來這裡接受敬水禮。另一位就是隆波,去謁見長老就是因為這本書。
這本書寫到:
「心往外送是苦因,
心往外送的結果是苦,
心清楚地照見心是道,
心清楚地照見心的結果是滅。
心的自然特性是必然往外送,
但心往外送之後沒有覺性,動蕩起伏是集(苦因),
心往外送以後,動蕩起伏的結果是苦。
如果心往外送了以後,
有覺性,沒有動蕩起伏是道,
然後得到的結果就是滅。」
最後第三段闡述:
「所有的聖者都擁有不往外送、也不動蕩起伏的心,
擁有圓滿的覺性作為心的家。」
措辭也許稍微有些改動,沒有完全準確,但第一段是很準確的,第二段因為較長,所以縮短了。
當隆波讀到這裡,心很震撼,因為之前已經看到了苦、樂、好、壞都是因為這顆心,不是因為身體,當讀到關於「心」的法時,心震撼,它抵達心。
然後看名字是「帕拉塔那坤威素提」(僧銜),那個時候尊者還是「帕拉塔那坤威素提」,後來才成為「帕拉差帕塔查然」(僧銜)。然後向人打聽這位尊者在哪裡,隆波也想跟隨他學法,但沒有人認識。
隆布敦長老是一位不太為人所知的高僧,隆波的剃度師是隆布敦長老的侄子,跟隨隆布幾十年了。他說:「起初,隆布敦過著清淨的生活,然後布拉帕蘭寺也沒什麼人來,後來是因為您,很多人才開始認識隆布,布拉帕蘭寺才有這麼多人來。」他這麼說並不是在批評隆波,他喜歡,他喜歡看到人們進寺廟。
打聽了一段時間,才知道他的名字是「隆布敦」。這次隆波查看了隆布敦的資料,查看資料,發現他是隆布範的老師。糟了!隆布範已經圓寂很多年了,那隆布敦長老還活著嗎?
直到有一天,有人說隆布敦長老還在世,當知道隆布在蘇林府的布拉帕蘭寺後,隆波立刻坐火車去找他,去跟隨他學法。於是他就教導修行的方法,在教導之前,他靜靜地打坐,大概四十五分鐘左右,然後睜開眼睛就教導:
「修行不難,難的是不修行的人,
讀很多書了,現在讀自己的心」
當聽到「讀自己的心」,心又再一次震撼了。
一開始是因為書,第一次有禪相生起,就關注到心。然後看到那本雜誌,心又再次受到震撼,它看到實相:如果心不苦,誰苦呢?在讀到隆布敦的「心的四聖諦」時,心也感嘆:「如果心不苦,誰苦呢?」
當見到尊者 尊者教導修行的方法:
「修行不難,難的是不修行的人,
讀很多書了,現在讀自己的心。」
關鍵詞就是「讀自己的心」!從那個時候起,隆波就努力讀自己的心。
一開始不會讀,尊者讓隆波像讀書一樣去讀心。尊者說要去讀這本書,讓隆波「讀」,但隆波卻努力地去「寫」書。修行人自稱觀心、觀心,但幾乎百分之百是在裝修心,而不是如其所是地觀心,喜歡裝修心!比如:當我們開始打坐時,觀察到嗎?當我們開始打坐,必須先裝修心,讓心一動不動,讓它模模糊糊、昏昏沉沉,然後昏沉到一定程度後就說:誒!今天修行很好。
修行好什麼啊!變成餓鬼、阿修羅還不自知,變成畜生也毫無察覺,坐著卻迷失,被愚痴籠罩;或坐著,然後被貪籠罩,變成餓鬼、變成阿修羅、執見者。
一開始 隆波也是修觀錯誤,去干預心,讓心一動不動、空空的。三個月後,向隆布敦長老做禪修報告。隆布敦長老說:「修錯了,重新修。讓你觀心,不是讓你造作心。心有職責去想、演繹、造作,你卻讓它不想、不演繹、不造作。修錯了,重新去修。」
以前的高僧大德便是如此的,不會教導得太長,只做簡短的教導。我們就必須努力、奮鬥。這次重新確立基礎:隆布敦長老讓我們讀自己的心 ,我們是讀者,不再是作者了,心是什麼樣子,就如其所是地知道它是那樣的。
做得到嗎?——「心是怎樣,就如其所是地知道它是那樣。」說起來很簡單,但實際上很難,因為忍不住要做,忍不住要做!有時候就做一點點,這樣刻意去做,然後去觀。如果是那些很用力觀的人,哎!感覺就像要咬人似的!
以平常心覺知自己、讀自己的心,讓心自然平常地運動變化及運作。
心是如何運動變化的呢?當眼睛看到色,心就會生起苦樂,生起善法或不善法,有覺性及時地知道。當看到美女時,心生起淫欲,知道「有淫欲」,而不是知道她很美。一般的人看到美女就是美女,我們修行人、觀心之人,看到美女心生起貪,有淫欲、喜歡她、愛上她了,及時地知道,知道這一點,稱之為「觀心」。
耳朵聽到聲音,聽到罵聲,心生起瞋,一般的人聽到罵聲,就會轉身去看:誰來罵老子?馬上就要跟他打架了。至於修行人聽到罵聲,心生氣,知道「生氣」,這就是「讀自己的心」,不是一味地關注外在的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,而是持續讀不斷變化的心——當眼睛看到色、耳朵聽到聲音、鼻子聞到氣味、舌頭嚐到味道、身體有接觸、心接觸念頭,就會生起樂、生起苦、生起善法、生起不善法,要有覺性及時地知道,不用對治它。
比如:我們聽到敵人辱罵我們,回頭看到他,就更加討厭他,更加生氣了。我們看到心正在生氣,那該如何是好?去對治好嗎?不用對治。瞋心屬於行蘊,在苦聚裡,對苦的職責是知道,而非斷。因此,心有瞋心生起,知道「有瞋」,直接去知道。
或看到美女,心生起欲貪,不用去斷它。欲貪也是行蘊,也屬於苦的範疇,是我們需要知道的對象,而不是要斷除的。但若欲貪更強烈了,貪欲更強烈了,發展成了「集」,變成了渴愛,這就必須斷除了。如果它剛開始生起時,若喜歡也沒關係,但如果「想要」生起了,想得到了、想要強搶她了、想要強姦她了,這就必須要斷了!「集」要斷!
「苦」要知道,「集」要去斷。「集」就是渴愛,渴愛是什麼?是力量很強的貪。但如果是一般的貪,喜歡這個、不喜歡那個,這個要知道,它屬於苦聚。因此,貪有兩種狀態,一個屬於苦的部分,如果貪很強烈,就變成「集」,變成渴愛,讓我們的心更加掙扎,這一點就要去斷了。
斷的方法,若是暫時地斷,就以覺性去斷,及時地知道現在心「想要」了,想去強搶她了、想去強迫她了,及時地知道,渴愛就會滅去。無論如何,渴愛都是煩惱習氣,如果我們有覺性,煩惱習氣就無法存在,渴愛就會滅去。
斷除渴愛,只有在斷除無明後,才能徹底斷除,必須具有極大的智慧,極大的智慧就是「明」,徹底地明白四聖諦。如果明白四聖諦,渴愛就不會再生起,這是斷渴愛,透過讓渴愛無法再生起的方式。因此,不用反覆地去斷,一斷永斷,僅是在我們內心斷除邪見,就可以滅除無明,無需特意斷除渴愛,因為渴愛已經不會再次生起了。
觀心,它很細緻,慢慢地去觀。起初就持續、簡單地如實觀心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接觸所緣,心苦、心樂,及時地知道;心喜歡、不喜歡,及時地知道;心貪瞋痴,及時地知道;心是善,也及時地知道;心是不善,也要及時地知道。比如:看到尊者托缽,心是善,想第一個去供養尊者,心具有很大的功德,但被別人搶先供養了,就覺得我們的功德不圓滿了,一開始功德滿滿,現在缺了一點點,這已經變成了不善法,已經變成了貪。
因此,我們的心是善的,及時地知道;善完成了,我們歡喜,也要及時地知道;我們的善沒有完成,傷心,我們也要及時地知道。
持續覺知自己,苦、樂、好、壞,不斷地去知道,最終有一天,智慧就會生起。初步階段的智慧就會生起(明白說):心不是「我」。當心不是「我」,心的產物——五蘊,也不是「我」了,周圍的世間萬物也不是「我」了。
因此,僅要斷除對心的邪見,就可以斷除所有的邪見了。因此,斷除煩惱習氣,當聖道切斷煩惱習氣時,是切斷在心。當心清洗了邪見,所有一切、全部的五蘊、全世間 就沒有「我」了,因為心不是「我」。
然後接著修行下去,智慧就會更強大,就會看到:色法的部分。色法沒有什麼,色法僅有苦,心就能夠放下色法。當能放下色法,就能放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當能放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了,欲貪和瞋恚就不會再生起了。
因為如果我們依然執取眼睛……為什麼執取眼睛?因為眼睛讓我們看見令人滿意的色,當我們看見——眼睛亦無實質,那麼眼睛所見的色,又怎麼會有實質呢?我們便能看到內根和外塵: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;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 並沒有什麼,僅有物質,內根和外塵兩者皆是物質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 是內根,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 是外塵,別無他物,僅有苦。
何時能看到此身是苦,就能放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,放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,欲貪和瞋恚就不會生起了,它們是以「不會再生起的方式」被消滅了。它們不再生起,是因為我們徹底明白了色,明白了這個身體,直至我們沒有了對身體的執取。
然後繼續修行,直到最後階段,修行的範圍就會縮小至「心」,最後就會看到——心自身也落於三法印的法則,沒有執取心,就沒有執取五蘊,也沒有執取世間。
初果聖者的階段和阿羅漢聖者的階段是有所區別的:初果聖者斷了心是「我」的邪見。因此,沒有什麼,五蘊和世間都不是「我」;阿羅漢沒有執取心,因此就沒有執取五蘊,也沒有執取世間的一切,什麼都不執取了。因此,我們觀心,要觀到可以抵達心的程度。
有些人說觀心,然後去專注心,讓它一動不動、空空的。這不是觀心,這是在緊盯「空」。因此, 修習就要修得正確,它不難的,難是因為修得不對、修得不夠。
今天的講法就到此。
【完】
聲明:
由於受到語言以及個人修證水平所限,跨越語種後很難如實還原隆波帕默尊者的本意。譯作若有任何不精準之處,完全歸責於我們,歡迎大家不吝指正。
影片(字幕):